哔——时代变化太快,很多事和词都需要重新定义。
Papi酱在视频里骂人,为什么这么值钱?因为这是人类的共性。Papi酱的往期视频被下架整改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据说是因为视频里出现了广电总局明令禁止的粗俗语句。得把不当的部分全都处理掉,视频才能重新上线。
这已经不是啥新鲜情况,看过康熙来了和奇葩说的人都知道,主持人和现场嘉宾说得太嗨收不住的时候,一些不该让观众听到的话往往会被后期给“哔——”掉,也就是经过了消音。而被消音掉的那些词句,通常就是脏话。
美剧也是这样,《破产姐妹》里,每当Max要说出那个F开头的四字单词时,配音就变成了“哔——”,字幕中跟在F后面的两个字母也变成了星星,徒留Max一个空荡荡的嘴型。
为什么用“哔——”而不是“滴滴叭叭呜”?
电视工作者们管“哔——”这个声音叫“千周”,就是1KHz声音信号的意思,它属于电视系统里面唯一的声音预置信号,用来表示真正的“空白”,它告诉你的耳朵“前方注意,这段马赛克,这段马赛克。”
为什么使用“哔——”而不用“滴滴叭叭呜”、“哐叽哐叽”等其他的声音?因为“哔——”这个声音是单频的,它只含有一种频率。由于自然界中不存在单频的声音,所以制作者用这种声音来表示这是后期加工的,与自然界中的所有声音区分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动画片《兔八哥的故事》中有只BB鸟,它的叫声就是“哔——哔——”,整天被歪心狼追着跑,这应该是“哔——”这个声音最早一次在电视史上大规模出没。
据说麦当娜在美国一次超级碗的直播上连续爆了很多粗口,由于超级碗的直播面向全美,观众不分老少,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段爆粗口的片段,大家难以适应。于是美国制定了一项新闻审查制度,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要延时几秒播出,好让导播有时间判断前方是不是有脏话出现,该不该按“哔——”。
粗口亚文化
可见“哔——”的存在前提就是脏话。
从小大人们就教我们要抵制脏话,我们乖乖听话了,把世界上所有脏话当成恶毒的指向,看到小朋友说脏话就报告老师,路上听到有人骂脏话就捂耳朵走开。总之,脏话无所不在,却又让人讳莫如深。
直到有一天,我们从自己的父母、老师口中听到了不小心飙出口的脏话,目瞪口呆。
你开始发现,说脏话在一些场景里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说“他妈的”(请各位看官自动将本文相关粗口转换为哔——)并不是真的对谁的妈妈有意见。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在借助脏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比如“我操”(我哔——,此处再次提醒下),它基本上能表示“惊讶”“感叹”“欣喜”“悲伤”……总之,任何在当时语境下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那一瞬间情感的词汇,都可以用“我操”来代替。虽然说完“我操”之后,你的生活也许并没有什么变化,压力的释放却能让你快乐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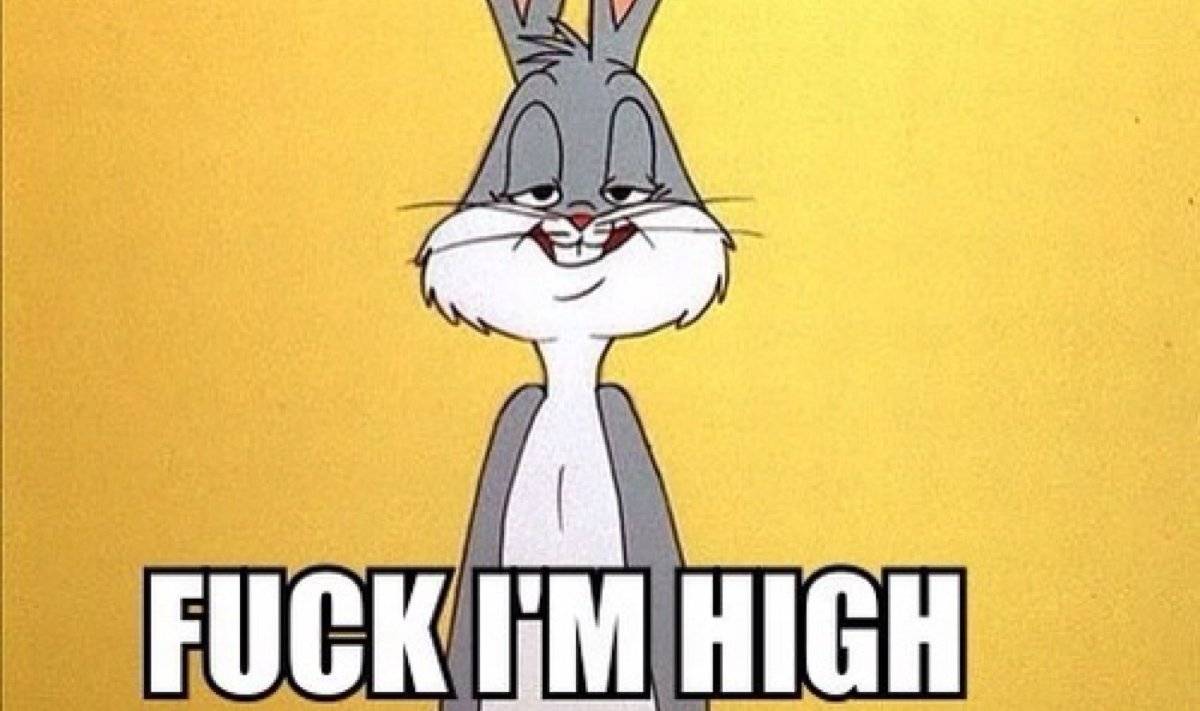
还真的有人在认真研究脏话。一个叫奇普·洛的美国人创办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他主张严肃对待脏话,“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骂人的词,欢迎骂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杰认为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痛剂,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一句恰到好处的“他妈的”甚至能胜过千言万语。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鲁思·韦津利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写到了她对脏话变迁的研究:“如今要好几个fuck才能达到一个fuck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越来越能理解脏话存在,也越来越能理解脏话的产生机制和所能带来的后果。
粗口和脏话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人们使用它、讨论它、接受它,说到底,粗口不过象征着隐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天性,人人天生拥有“说脏话”的技能。
权威者们的脏话
毕达哥拉斯在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他妈是怎么想出这个定理的?”

天呐,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生活在约莫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希腊,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脏话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正经历史记录当中。
再看看我国,在古代就存在着专门用来骂人的“詈(lì)词”,在汉语的书面语里,也有专门的“詈词”,但因为经过了文人的筛选修饰,现在看起来大都比较文明。
比如《战国策·赵策》中,齐威王骂人骂得最狠的那句“汝母婢也”,意思不过是说“你妈是小老婆”。范增给不听劝的项羽逼急了,才憋出“竖子”两个字,就相当于骂项羽是小屁孩儿。
到近代,权威者们谈起脏话来就没那么遮着掩着了。鲁迅写《论“他妈的”》公开讨论国骂,蒋介石在各种会议上张口闭口“娘希匹”。
美国前总统沃克·布什回忆他1975年10月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时的交谈,他回忆道:“……毛泽东在外交会谈正常进行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论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放狗屁’还无关紧要。他的一位负责的女翻译照翻不误。这个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话词汇中也找不到。”

老布什:“这个哔——我给满分不怕你骄傲。”
他们都在说脏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连父母、老师这种象征着权威的身份也会说脏话,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说脏话正是人的天性啊。
来自“哔——”的保护
在一些封闭场景中脏话并没有问题,但是让不该听脏话的人听到脏话,那就目瞪口呆了。
所以很多时候,为了避免“不适合脏话”群体目瞪口呆的情况出现,还是得用“哔——”的手段来达到某种保护的目的。电视节目中受访者由于情绪激动等原因说出一些不雅的言辞,或者剪辑是隐蔽拍摄,画面中人物语言习惯带有脏话,这些话就面临着被“哔——”的命运。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就很难见到下一个像Papi酱这样在视频中用“册那”来调侃方言的人了?毕竟“册那”本身就一句经典沪骂。其实要让节目有人情味儿又能顺利播出,让可以观看的群体看到,让不宜观看的群体看不到不就完了嘛。
不过在媒体审查制度尚未完善的当下,我们还是先好好接受来自“哔——”的保护吧。反正被“哔——”掉的那些内容——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随便哪个操蛋的白痴都懂。







 400 6900 328
400 6900 328



